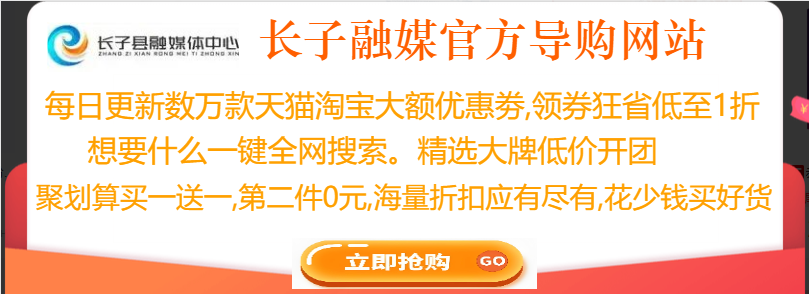《长命》这部作品经过十年的培育,作家对故事倾注了极大的心血。刘亮程在50岁那年,于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邂逅了这个故事。在这漫长的十年间,他始终居住在村庄之中。对于写作,他坦言更偏爱木工技艺。他日复一日地从事着泥瓦匠、设计师、菜园农夫、果树修剪工以及泥巴制作等工作,双手辛勤地劳作在土地之上。在虚构的领域中逗留久了,便需要回到现实世界一探究竟,他尤其喜爱聆听斧头砍伐木材时产生的震撼回响,那声音宏大而真实,足以令人陶醉。
居于乡村之中,他体会到了一种安宁,“村里既有比我年长十岁、二十岁的长者,也有比我年轻十岁、二十岁的后辈,我恰好处在中间位置。一群长者如同岁月的寒风般吹拂而过,而另一群青年则紧随其后。”在此,他目睹了时间的流转,感受到了岁月的变迁,见证了生命的诞生与消逝,以及生与死的轮回。
当神婆魏姑这一角色登场之际,《长命》的故事便逐渐苏醒。与《本巴》相仿,刘亮程表示,《长命》的创作初衷亦在于解答梦中的困惑。他坦言:“在梦境中,我孤独无依,尚未成熟,未曾获得力量与勇气,仍旧胆怯,仍旧被追逐。相较现实,我更倾向于关注梦境的作家,梦境中存在另一个自我,梦境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另一幕戏剧。”
对批评家来说,剖析刘亮程构建的小说领域颇具挑战性。王鸿生评论道,刘亮程不断拓宽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,这是一个既超越现实又超越历史的,始终如一却又不断变化的领域。这样的世界不倾向于被观念化或过度解读。它融合了动物、植物、自然界的风、尘土,以及漫长夜晚、日月星辰,还有神秘的野鬼、飘渺的魂魄、梦境和坚硬的石头等既具体又抽象的元素。如今,又添入了家谱、牌位、神秘的巫婆和悠扬的钟声等象征。其内涵不断丰富,情感愈发深沉。他指出,在小说的语言运用上,刘亮程偏爱简洁直接的短句表达,这种写作手法实则是一种反常规的比喻,他将其形容为“一场既质朴又充满挑战的文学探险。”
许多人对刘亮程的了解可能始于《一个人的村庄》,评论家郜元宝也不例外。他赞同王鸿生的观点,即刘亮程的创作领域超越了人类,“他不仅紧贴人物进行描写,更是紧贴自然与宇宙进行书写。他不仅讲述人的故事,还讲述灵魂、神灵和鬼魂的故事。”他坚信,刘亮程至今的写作,实际上是在持续地重新诠释他对“村庄”以及中国某个特定“地方”的认知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与张炜的《融入野地》、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以及毕飞宇的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并称,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宝库中的瑰宝,蕴含着深邃的灵性。然而,郜元宝对此却抱有更深的疑问:从这等罕见的高起点出发,刘亮程能否继续前行?他能否跨越“村庄”的界限,探索其他“地方”?若他真的踏足他乡,他又将以何种方式重返“村庄”?他究竟将怎样描绘“时代”、“历史”、“过去”和“未来”这些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、不断流动的时间维度?

《长命》首发于《收获》
《长命》这部作品,通过文学手法延展了生命的长度,映照出人存在的深层内涵。正因如此,它能够激发起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童年、家谱的共同记忆。在阅读《长命》的过程中,评论家张新颖不禁回想起自己在胶东农村度过的童年时光,他认为那里的居民并非缺乏精神生活,相反,他们拥有着独特的内心世界。在他眼中,刘亮程的叙事语言超越了常规与束缚,既融合了散文的流畅,又蕴含了诗歌的韵律,更是贴近日常口语的质朴。他并非仅仅关注人物刻画,而是深入到他的生活领域,生动地展现了生活的本真面貌。
项静评论家指出,《长命》一书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探讨,特别是关于萨满文化的传承者魏姑这类人物,她们通常为女性。她强调,乡村社会缺乏心理学知识,在应对所谓的“假病”或“虚症”时,村民会采用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。她亦提出疑问,《长命》的叙述速度较为平缓,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,短视频风头正劲,对于一位刚崭露头角的作家而言,他们又当如何保持内心对于文学叙述节奏的坚持?
魏姑开启了《长命》的故事篇章,她所扮演的角色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青年评论家吴天舟曾指出,魏姑这一形象,既展现了对人世与鬼域的深刻批判,又透露出一种深沉的孤独感,她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孤独的存在。方岩这位青年评论家认为,《长命》描绘了两个世界的交织与交流,他特别强调魏姑的游历、编纂家谱、以及她一直在打造的钟,这些都象征着对历史传承与个人关系的某种重塑与延续。青年评论家战玉冰同样赞同小说中钟声的传承,“那座巨大的钟虽然被击碎,却化作了无数细微的声响,宛如某些即将逝去的传统,依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,持续不断地回荡,传递着它们的声音。”
小说中贯穿的家族谱系在不少现代年轻人眼中似乎已经不复存在。青年评论家刘欣玥在谈论此事时,提及她的祖父与外祖父大约在年近八旬之际,各自着手重修族谱,这一经历使她对自己的根有了更深的认识。“身为都市中的一代,我们早已习惯了将异乡视为故乡,很难讲与哪片土地有着非同寻常的归属感与联系。”《长命》这部作品描绘了“迁徙的人”与“失散的土地”如何在不可逆转的、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,重新找回彼此的联系。阅读这部小说时,让她深受感动的还有,魏姑对韩连生的那份深情倾诉,持续了数十年,如同一日,这种倾诉让刘亮程“善于抒发”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魏姑年已五十,却仍保持着少女般陶醉的、天真无邪的语气。在今天这个时代,这种近乎不可思议的浓烈情感中,究竟蕴含着什么?魏姑对韩连生的深情,实际上反映了刘亮程对西北大地的深厚感情,正如张新颖老师所言,那是对“生活世界”的深切热爱。
陆志宙作为一位出版人,致力于向读者揭示小说出版背后的种种故事。以评论家们讨论的钟声为例,她们为了深入理解这一元素,搜集了世界文学中关于钟声描写的文本进行深入研究。“我们希望探究《长命》在何种文学脉络中得以理解,进而明白为何这部小说成为刘亮程六十岁时的‘天命’之作。”
这十年间,我放下了虚构的幻境,逐字逐句地触摸那些曾在我笔下流淌的文字。那个金色的秋天,饱满的麦穗,那个清晨,那个傍晚,现实世界如同细水长流般,缓缓地回到了我的生活之中。在刘亮程看来,无论人间的故事多么漫长,终究是短暂的,是肤浅的。对于作家而言,他们始终面对的是一个无尽的空白,《长命》亦如此。他言:“在创作《长命》之际,众多生灵已逝,诸多往事已成定局。然而,我决心以一部著作,重现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,让逝去的生命得以重生,让死者得以再死。这便是文学的力量。《长命》承载着我的生命,也承载着那片土地上人们的故事。”期望《长命》一书能够为那些已经逝去的先辈,以及与我们血脉相连、情感深厚的这片土地上的文化、传统,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。